老人的智慧??读杨绛的《走到人生边上》 - 汉语
2007-11-09 来源: 东方网-文汇报|http://www.eastday.com.cn/ 我要评论(0)
两年前,杨绛先生住了一次医院,躺在病床一直在思索一个题目:《走到人生边上》,出院回家后“好像着了魔,给这个题目缠住了,想不通又甩不开”,于是找来许多中外文的参考书,开始动笔。终于在两年半与老、病、忙的斗争中写成了这本书。书分两个部分,前面一部分是论述,后面是“注释”,其实是独立成篇的散文。
“走到人生边上”,照杨先生的解释,再往前走,就是“走了”、“去了”。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,行将走到生命尽头,对人生的回顾,对人的本性、生命的意义,对生与死、灵与肉等种种问题的思索。苏格拉底曾经说:“到了肉眼开始朦胧的时候,心眼才锐利起来。”老人的智慧,是人生经验的结晶,杨先生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探讨这些玄理的,所以读起来趣味盎然。我这里挑几个小片断,向读者介绍杨先生的这本新书。
关于“神鬼”
杨先生的父亲不信鬼,钱先生和他们的女儿从来不怕鬼,但杨先生从小就怕鬼,住在清华园的时候,家人把清华几处众人说鬼的地方瞒着她,免她害怕。后来搬进城里才告诉她。杨先生说:“我知道了非常惊奇,因为凡是我感到害怕的地方,就是传说有鬼的地方。”从她家到温德先生寓所要经过横搭在小沟上的一条石板,有一天晚上,杨先生独自一人经过,却怎么也不敢过那条石板,三次鼓足勇气想冲过去,却像遇到“鬼大墙”似的,感到前面一片黑气,阻止她前行,只好退回家。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年日寇屠杀大批战士和老百姓的地方。
“我本人只是怕鬼,并不敢断言自己害怕的是否实在,也许我只是迷信。但是我相信,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而断为不存在。这话该不属迷信吧?”以不迷信的心态说鬼,是个好办法。我们不妨也以不迷信的态度,听杨先生说鬼。
关于“命理”
命有没有理?杨先生还是以不迷信的态度谈论这个问题。她小时候碰到过一个算命的瞎子,拿她刚刚去世的弟弟的“八字”给他算,瞎子掐手一算,摇头说:“好不了,天克地冲。”又拿她姐姐的已经夭折的孩子的“八字”让他算,瞎子掐手一算,勃然大怒说:“你们家怎么回事,拿人家寻开心的吗?这个孩子有命无数,早死了!”
杨先生与钱先生结婚后出国,钱先生的父亲拿了一份钱先生的命书交给她,开头说:“父猪母鼠,妻小一岁,命中注定。”杨先生确实比钱先生小一岁。但最后说:“六旬又八载,一去料不返。”批语:“夕阳西下数已终。”抗战时钱先生有个学生,曾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“铁板算命”,后来也给钱先生算过,算出来的结果和那份命书上相仿,只是命更短。“文革”中钱先生曾大病一场,据那位算命的学生说,钱先生那年可能丧命。但钱先生最后享年八十八岁,足足比命书上算的多了二十年。“不知那位‘铁板算命’的有怎么解释。”杨先生终究是不迷信的。杨先生应该读过《了凡四训》吧?这并不难解释。
杨先生曾写过一篇回忆“文革”初年经历的文章,题目叫“丙午丁未年纪事”。丙午、丁未是一九六六、一九六七年。中国以前有一种说法:丙午、丁未,从古就是凶年。据说是因为“丙丁属火,遇午未而盛,故阴极必战,亢而有悔也”(《池北偶谈》)。宋代有人编了一本书《丙丁龟鉴》,把一千多年来的所有丙午、丁未年发生的灾变编在一起。我当时看到杨先生那篇文章的题目,就想到杨先生一定知道丙午丁未为灾年的说法,所以才特别标明丙午丁未年,现在读了杨先生的这本书,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。
《论语》
书中引得最多的是《论语》,杨先生对《论语》有很独特的见解。
杨先生说《论语》最有趣。“读《论语》,读的是一句一句话,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,书里的一个个弟子,都是活生生的,一人一个样儿,各不相同。”钱钟书先生曾对杨先生说:“你觉得吗?孔子最喜欢子路。”杨先生也有同感,孔子最爱重颜渊,但偏宠的却是子路。子路聪明有才能,对孔子最忠诚,经常在孔子身边,为人言行最为真率。孔子常常不由自主地称赞他,但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,不像对其他弟子那样总是很有礼。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前不久出了一本谈《论语》的书《丧家狗》,颇引起一番争论。在谈到孔子与其弟子的时候说,孔子对学生有夸有骂,夸得最多的是颜渊,骂得最多的是子路,子路挨骂,但忠心耿耿,他和孔子,有点像李逵和宋大哥。李零终究没有说到孔子其实最偏宠子路,这一点似乎不及钱先生和杨先生看得透彻。
其他弟子,子游、子夏,孔子也喜欢,爱和子游开开玩笑,对子夏多鼓励。子贡最聪明,孔子和他谈话很有礼,但是很看透他。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。最傲的子张,门弟子间唯他最难相处。陈亢是最无聊的弟子,从未向孔子问过一句话,却总在背后打听孔子。
像杨先生这样读《论语》,当然“是一本有趣的书”。
劳神父
在谈到灵与肉的统一问题时,杨先生想到了小时候认识的一位天主教的神父,是“克制肉欲,顺从灵性良心的模范人物”。这就是以前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创始人劳神父。在“注释”里,杨先生又专门写了一篇回忆劳神父的散文,说自己小时候,除了亲人,最喜欢的是劳神父。杨先生读的是启明女校,正是天主教办的学校,劳神父大概也在那里教书吧。杨先生读大学时还回过一次母校,见到了大胡子已经雪白雪白的劳神父。那是一九三?年,劳神父八十岁,杨先生十八岁。
我查了相关资料,才知道劳神父中文名字叫劳积勋,法国人,生于一八五八年(其实一九三?年时才七十二岁),十七岁入耶稣会修道。清光绪九年(一八八三年)秋来沪。后回国续修天文等科学并攻神学,晋司铎后,于光绪二十年再度来沪,任徐家汇天文台副台长。后任台长,长达三十七年之久,著有《远东大气》、《六百二十次飓风的路向》等书。一九三一年九月回国,法国总统授予四级荣誉勋位,英国国王授予骑士勋章。次年在巴黎去世。
杨先生在书中说:“上海至今还有一条纪念他的劳神父路。”劳神父路初名天文台路,一九二七年改为劳神父路,一九四六年起早改名合肥路了。
书报
杨先生为了写这本书,找了很多参考书,有以前读过的,如《四书》、《圣经》,有以前从未读过的,如美国白璧德的作品、法国布尔热的《死亡的意义》。书里还引到一些图书报刊,都是近年新出版的,如中国电影出版社二??五年出版的《弗洛伊德的智慧》、二??五年第三期《读书》杂志、二??五年三月号的美国《国家地理杂志》,提到的报纸有两种:《文汇报》(二○○六年十月十八日)和《新民晚报》(二○○六年五月二十四日)。九十六岁高龄的老人,如此读书看报,学而不辍,真让人肃然起敬。
顶一下
踩一下
回首页
相关新闻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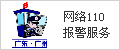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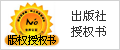
网友评论
匿名用户 验证码: